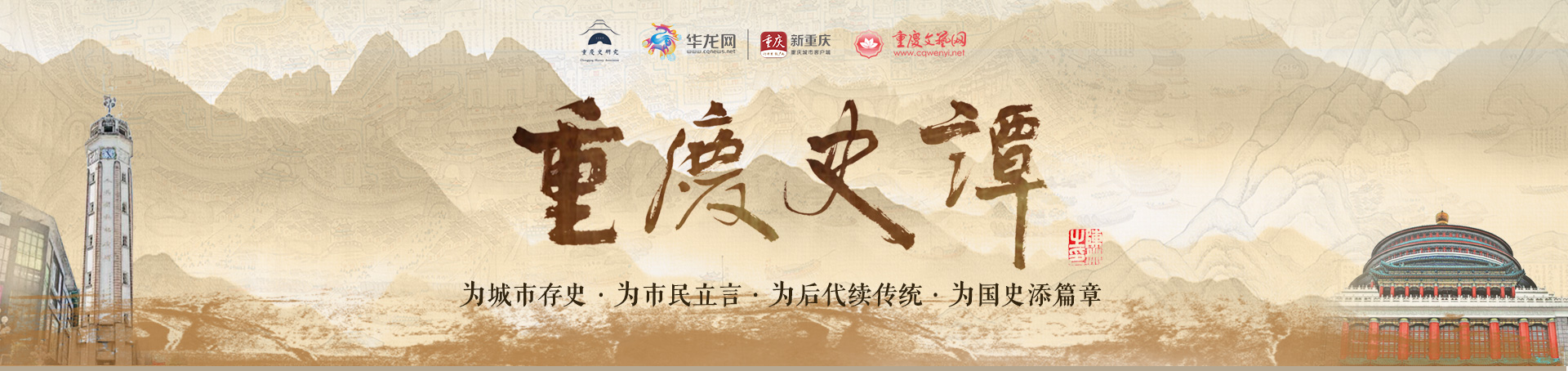

新年之际,喜读周勇教授主编的《重庆通史》,在高兴与振奋的同时,谨向重庆市地方史研究会的领导和学者们致以热烈的祝贺和深切的敬意。
《重庆通史》是一部份量重,质量高的学术著作,难能可贵。
底气充足,此难能可贵者一也。
随着中国区域史研究蓬勃开展,学术界对重庆史的研究有浓厚的兴趣,倾注了大量心血,产生了大量研究成果。1978-1998年间出版的有关重庆历史的著作就达701部,发表的论文、资料达8042篇。重庆市地方史研究会的学者们对重庆史更是进行过深入的研究,他们曾与四川大学合作完成了国家“七五”期间哲学社会科学重点课题《近代重庆城市史》,直接编撰出版了重庆史著作74部,论文、资料500多篇,从而为《重庆通史》提供了丰富的思想与资料,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正是这充分的前期准备,丰硕的学术成果,扎实的研究基础,才产生了这部长达115万字的学术著作。所以《重庆通史》决非急就之章,更非潦草之作,而是一部集思广益,深思熟虑,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力作。
班子强劲。此其难能可贵者二也。
《重庆通史》有一个老中青结合,学术实力强劲的班子。老一辈领军人孟广涵、周永林同志长期致力于重庆史的研究与组织工作,广涵同志曾任《近代重庆城市史》的顾问组长,永林同志是该课题负责人之一。如今,年过八旬,仍老当益壮,研究重庆历史之志毫不稍懈,尊重人才,奖掖后进,联系学者,不分中外,有“天下英雄入吾彀中”之气慨。《重庆通史》的主编周勇教授,得其父永林同志之严格家教,勤敏好学,敬业乐群,学风朴实,思路开阔。20世纪80年代初,就学于四川大学历史系时,由我指导他写作毕业论文,后又同他合作写成《重庆开埠史稿》,他才华初露,研究重庆历史的方向亦由此明确。上世纪80年代后期,他作为《近代重庆城市史》课题组学术秘书、主研人员之一,着重研究重庆作为长江上游经济中心的形成与发展,表现出了强劲的研究实力,为他如今主编《重庆通史》做了扎实的准备。课题组成员胡道修、胡大牛、张瑾也毕业于四川大学历史系,“科班出身”,学有专长,进步迅速,已成骨干。有老一辈学者领军前进,有好的主编集腋成裘,有中青年学者实干苦干,加上学术界同仁的关注支持,这种强劲的合力效应必然产生优秀的成果。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他们把研究《重庆通史》看成“是重庆历史学界特别是地方史学界的历史责任”,“神圣事业”。这种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使他们能够谦虚谨慎,把自己的成果看成是“20年来重庆地方史学界学术研究成果的总结”和“集中体现”。海纳百川,有容乃大,顾全大局,团结合作的精神难能可贵。
原创性强,此难能可贵者三也。
《重庆通史》的作者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结合本地区的历史实际,突出了地方历史的特色,在历史分期问题上的见解,便集中体现了鲜明的原创性。
中国是一个土地辽阔,历史悠久的大国,社会经济发展是极不平衡的,各地区的历史发展既有统一性又有特殊性。中华民族是多元一体的,中国历史文化也是多元一体的。因此,我们研究历史时,既要重视历史发展的统一性,也要重视历史发展的多样性,既见森林,又见树木。
《重庆通史》既按中国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来叙述重庆发展的历史,又在近代史的分期上有自己的独到见解。他们不套用1840年为中国近代史开端的说法,而是将重庆近代历史的上限定在1876年《烟台条约》――1890年《烟台条约续增专条》――1891年重庆开埠这样一个历史过程里。这个断限是符合重庆的历史实际的。重庆是一座内陆城市。由于地理和交通的独特性,比之上海、广州、天津、武汉等城市,遭受列强直接侵略的时间要晚一些,程度上也有差别。1840年鸦片战争以及以后的30多年,整个四川仍然在封建社会是酣睡,重庆还是一座封建城市,尚未跨入近代城市的门槛。只有经《烟台条约》――《烟台条约续增专条》――被迫开辟为通商口岸的15年时间,才被迫向世界开放、开始走进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关于近代史的下限,该书也没有定在1949年而定在民主革命任务彻底完成的1952年,这也是一种创新的表现。
江泽民同志在考察中国社会科学院时提出了“努力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重庆通史》应被看成实现这一目标的艰苦努力和有益探索。
新的起点,此难能可贵者四也。
《重庆通史》写的是重庆的历史。重庆历史是向前发展变化的。特别是直辖以后重庆的发展速度更快。老重庆成了新重庆、小重庆成了大重庆。写历史的人也有历史的局限性。如何跟上重庆发展的步伐,写出重庆不断前进的历史,这部《重庆通史》还只能说是一个新的起点,好的开端。作者们在完成这部著作的同时,在反思,在前瞻,提出了写新重庆、大重庆历史的展望。如今的重庆市,大城市与大农村并存。如何写出大城市的中心作用以及重庆市的城乡互动,乃至重庆与上海、武汉、成都等长江流域大城市的比较研究,浓墨重染重庆特色等等,还是任重道远的。1952年以后的50年历史是精彩纷呈的,有许多历史过程和历史经验与教训,这些都尚待历史研究者去描绘与总结,为加速重庆市的建设提供思想动力和理论支撑。
我期望周勇教授等年富力强的学者能毅然担负起这一任务,将《重庆通史》扩大容量,延长时段,加强论证,使之内容更加丰富与深刻。如今,周勇教授们已认识到了这一点并有所规划。望他们学无止境,前进不已,不断攀登历史科学的高峰。
(隗瀛涛,四川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四川省文史研究馆馆长)
重庆市地方史研究会编《<重庆通史>评论集》2003年印行